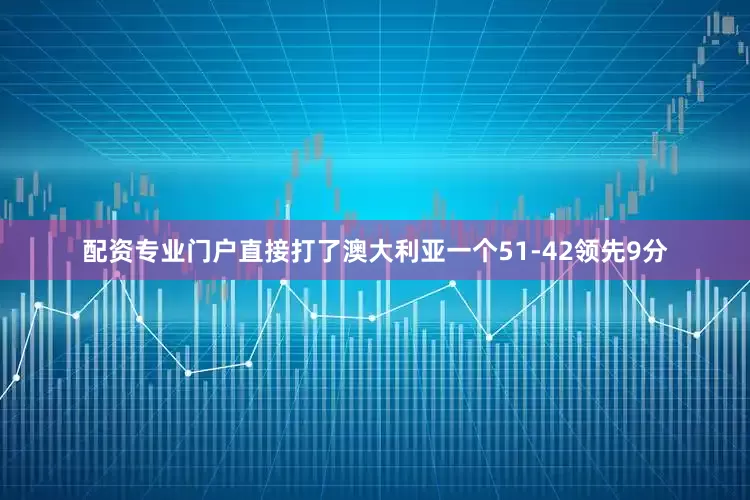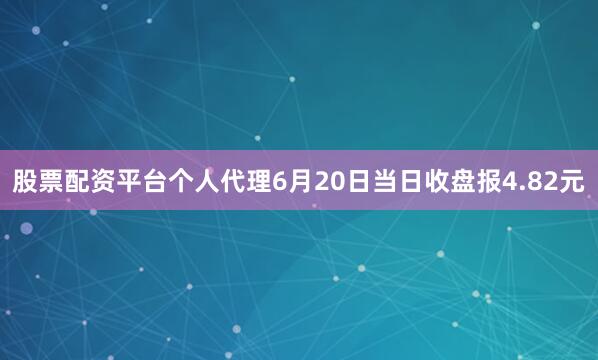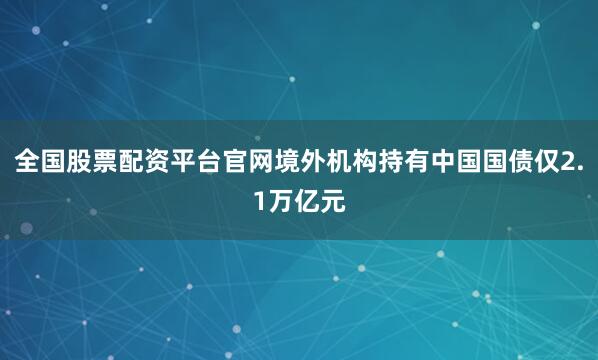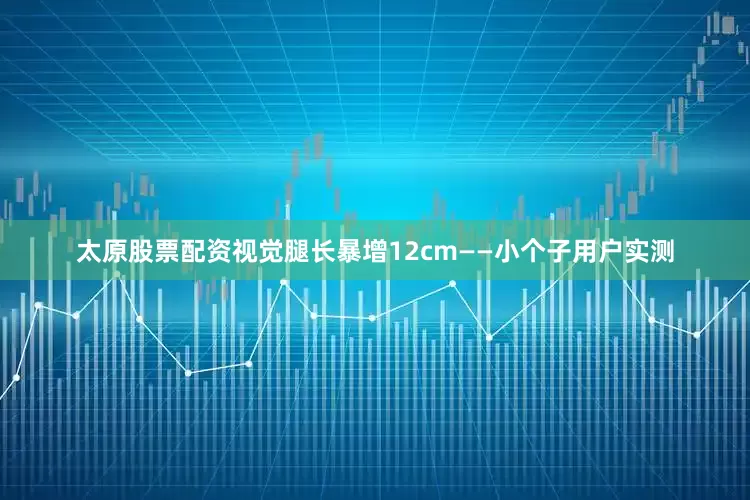潮新闻客户端 钱江湾
写过西湖之云的小文在潮新闻刊发后,一位异地的文友发来微信打趣:“西湖的夏云虽美,还是比不过古诗中的夏云呀!”的确,千百年来,诗人对夏云的描摹从未停歇。在35度以上的杭州夏日,躲在空调房里翻读着古诗,那些文字里的云影,似乎像加了少许薄荷的绿豆汤桃浆水一样,把暑气滤出了一丝丝的清凉。
(一)
魏晋时的陶渊明最懂夏云的神韵,他在《四时》一诗里的“春水满四泽,夏云多奇峰”几个字,堪称写夏云的神来之笔。夏日午后对流旺盛,云团在高空聚散无常,时而如孤峰插天,时而如群峦绵延,阳光穿过云层时,明暗交错的光影让“奇峰”更显立体。
展开剩余90%那天我站在杭州的吴山江河汇观亭上观云,看那些棉絮般的云团慢慢堆成玉皇山的轮廓,晓得了诗人为何能从变幻的夏云中读出山川气象。现在看来,说“夏云多奇峰”好像完全是写实之句,难度系数在1.0以下,但第一个人在1500多年前写出这样的诗,当属神来之笔,殊为不易。因为这首诗传颂太广了,以至于后人对作者还存在争论,许多人认为这种“诗中有画”的风格当出自东晋画家兼诗人顾恺之的手笔。
晚唐诗人曹松的《夏云》则像一部云的纪录片:“势能成岳仞,顷刻长崔嵬。”清晨推开窗时还是疏淡的几缕云丝,早餐后再抬头,已化作巍峨云山,连归巢的鸟儿都飞不到顶。
杭州的夏日常有这种奇观,城西的云团从龙井山后涌出来,半小时就铺满整个天空,又被江风忽然吹散,露出湛蓝的底色,正应了他“瞑鸟飞不到,野风吹得开”的续句。诗人站在原地“看忘回”,一天之中云彩变幻,目不转睛地凝望,可能早已忘记了时间的流逝,也忘却了自己正身处于酷热的盛夏里,这种由云朵之变到时光流转的联想,想必和现在杭州喜欢拍夏景的市民,举着手机相机到处追云的心情一样,瞬息万变的夏云之美谁不为之感慨系之呢?!
元末明初的天锡更是捕捉到了夏云的“脾气”:“拖雨驾雷翻覆顷,漏星藏月卷舒行。”杭州今年的梅雨季是前几天结束的。从梅雨季过渡到三伏天,雷阵雨会明显增多,特别到了午后说来就来。前一刻还是“奇峰”林立,转眼就乌云密布,雷声从钱塘江上传过来,豆大的雨点砸在车玻璃上。可雨停得也快,云絮舒卷之间,晚上月亮忽隐忽现,倒比晴空万里时更有韵味。有好几天的傍晚,钱塘江北的云被夕阳染成橙红,江南岸却飘着雨丝,朋友圈里许多人晒西湖的晚霞,也有人晒湘湖的雨帘,倒应了天锡诗里“千状眼前横”的热闹。
古人观云常常藏着生活的智慧。“天上鱼鳞斑,晒谷不用翻”这句谚语,在杭州的盛夏常能验证。那种像鱼鳞般整齐排列的透光高积云,是晴热天气的“通行证”。老人们看到这样的云,就知道可以把梅雨季晒不干的被褥搬出来,暑假在家撒欢的孩子们则盼着这样的好天气出去放风筝。
(二)
夏云在诗人笔下,从不只是一道风景,更藏着许多心事。南朝陶弘景婉拒梁武帝叫他息隐出仕的邀请,在《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》中说:“山中何所有,岭上多白云。”那份不恋官禄的淡然,像极了身边许多人对待云的态度:不刻意追逐,却总在抬头时与美好相遇。龙井村的茶农在炒茶间隙瞭望云天,灵隐寺的僧人在檐下看云卷云舒,也许都透着这种“白云自在”的心境。
我的一位至交老友几乎每周好几天的早晨,都要在孤山、苏堤和杨公堤一带跑步锻炼,有时兴起跑出个“玫瑰花”图案,让我羡慕不已。他手机中随拍下数不清风淡云清的西湖美片片,正如他的为人诚恳正直,眼里藏不得沙子。
我很早开始就喜欢王维的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那时还是读初中,并不懂得他诗中隐藏的许多禅意。他在另一首不那么有名的《欹湖》一诗中说:“吹箫凌极浦,日暮送夫君。湖上一回首,山青卷白云。”黄昏时依依不舍送别友人,在湖上回头一望,青山之间白云舒卷。浓浓的离别之情融入了壮阔山水之中,舒卷的白云藏着他豁达的胸襟。
在杭州的山中游走也有这样的体会。爬宝石山走到蛤蟆峰,累了索性坐在岩石上歇脚,看云从西湖上漫过来,掠过保俶塔的尖顶。翻腾的白云在湖山间循环,倒也能品出一点“坐看云起时”的哲理。杭州人夏天特别喜欢带孩子去九溪十八涧,那里的云团总绕着茶园缠着溪水,边玩水边看云,烦恼好像也随云飘走了。
盛唐诗人崔曙在一首送友诗中说:“寄心海上云,千里常相见。”远隔千里与友人的离愁别绪,都付予团团白云之中,深厚的情谊能够跨越千山万水。现在的人懂的更多的即兴表达。有一位朋友的同学暑期要到南美几国旅游,他在朋友圈里把杭州白云飘浮的照片发上去:“这是故乡的云,希望老兄也能多发那边的云山大片。”前两天小区里的大姐与在外地工作的女儿视频通话时,忘不了插播几秒傍晚窗户外的云:“你看杭州的云多好看。”夏云成了无形的纽带,不管人在何方,抬头望见相似的云,就像见了故人。
记不清是哪一个古人写的“霓霞映处慰孤鸿”,看样子有点从“缥缈孤鸿影”中延伸再创作的,反正我挺喜欢。傍晚的杭州,云被夕阳染成橘红、粉紫,武林广场和龙翔桥地铁站长廊下的人群,都成了这一幅幅油画里的点缀。
在生活里疲于奔波的人们,有时很像“孤鸿”一般茫然无助,可看到这样的“余霞散成绮”,心里总会感到片刻的柔软和温馨,原来大自然早已备好了安慰,就藏在抬头可见的云彩里。
(三)
说到夏云,忘不了苏轼笔下的旷达劲儿,像极了杭州人在酷暑里的从容。元丰六年,他在黄州写《水调歌头·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》,字里行间都是夏云的影子,读来竟和杭州的夏日如此契合。
“欹枕江南烟雨,杳杳没孤鸿”,江南的夏云也是这般湿润。杭州的云常带着水汽,从西湖或钱塘江上升起,像薄纱裹着远山。清晨站在柳浪闻莺,远看云气缠着雷峰塔,孤鸿在云里若隐若现,更明白“烟雨”不只是雨,而是云与水的交融。这种朦胧感,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都柔和了几分。
“山色有无中”化用了欧阳修的句子,被贬谪之人,看山看云都带着人生感慨,可这份“有无之间”的意境,倒和今人“凡事留余地”的性情相通,炎炎夏日总有一丝凉风冲你而来,云当浓时终放晴。就像杭州夏日里北高峰之巅常在云团里时隐时现,云厚时只剩下山尖和几根铁杆子,云散时又露出青翠的轮廓。
“一千顷,都镜净,倒碧峰”更妙。表面上江面平静如镜,倒映青山碧峰。此时的“云”藏于何处呢?其实就藏在“镜净”的水面之下。晴空万里时,白云与青山的倒影相映成趣,在澄澈的江水中清晰可见,恰似苏轼在逆境中仍保持的通透心境,不管外在的环境如夏云般变幻,但内心仍如江水般明澈,能保持定力不为所困。
西湖在晴朗的夏日很像一面镜子,云影倒映在湖面,与远处逶迤的群山倒影相映,分不清哪是云哪是山。云的变幻是夏日不可或缺的背景。“忽然浪起”的画面,在钱塘江畔也常能见到。积雨云从海上来时,江风骤起,白浪拍岸,打鱼的小船起伏不定,可杭州的船老大们见惯了这种阵仗,就像苏轼说的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,任云卷云舒,自有一种从容。
其实苏轼还写过好几首夏云的诗。如他在《和子由二首》中曾写道:“丹荔破玉肤,黄柑溢芳津。柳桥闲徙倚,藉草作茵褥。南风送落日,暑气随火云。”以“火云”形象地描摹了夏日傍晚的云,既写出夕阳壮丽的景色,又暗合暑气蒸腾的体感。诗人在湖边闲坐,看火云伴落日西沉,躁动的夏日不再感到酷热难挡,心里反而透着几分慵懒与平和。
元丰二年(1079),苏轼和近十位友人在徐州桓山雅集,以“春水满四泽,夏云多奇峰”抽签分韵作诗,苏轼抽得的是“泽”字,好写的夏云题材都被其他人抢去了,他自然写不了夏云,但他在诗中吟诵的“弹琴石室中,幽响清磔磔”、“悟此人间世,何者为真宅”仍然折射着我们夏日寻幽的影子。以“夏云多奇峰”作“命题作文”,本身就充满了向往夏云的浪漫志趣。
(四)
古诗里飘着的夏云,与我们隔着千年的时光,心情倒有几分相似。现在只要每天有好一点的云彩,朋友圈里都会自发举办“云展”大赛。有人说北山路的云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场景,有人不再满足于西湖西溪的“棉花糖”,专门跑到湘湖先照寺和三江汇上拍人无我有的大片,还有人把云团P成猫咪的样子。古人说“立地看忘回”,今人“举机追不停”,千年同此心,都被夏云的美迷住了。
杭州过几天马上进入初伏,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。与此同时,夏云精彩率也更加的高,人们对追云的愿望随之更迫切。早上看云识天气,决定要不要带伞;中午看云盼凉风,盯着云影在办公室窗上移动;傍晚追晚霞,哪怕被蚊子咬也要拍拍拍。古人从云里读出四季的流转,现在的我们从云里找到的是生活的小确幸。那天到西湖文化广场闲逛,看到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女儿,举着手机拍云彩,她对女儿说:“每朵云像不像都在对着我们说话呀!”
是啊,夏云从古诗里飘到今天,形态未变,那份让人忘忧的力量也未变。高温天抬头看云,心里总装着那么多的想象,那些像奇峰、像鱼鳞、像火烧,像什么也说不上来的云团,是大自然赠予每个在酷暑里奔波的人最大的安慰。就像王菲唱的“有人放烟花,有人追晚风”,世界赠予我酷热,也赠予我精彩。只要心里有一片晴空,总会拥有一个迷人的夏天。
发布于:浙江省场内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